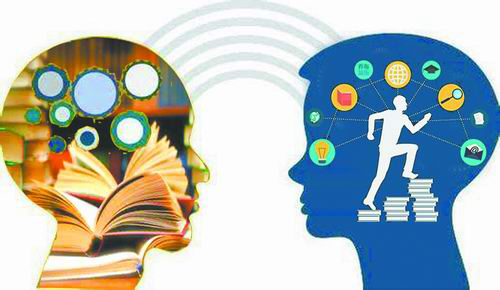
接上文,从案例开始讲述:
H.M.在冰上滑倒以后,需要一支拐杖,而这支拐杖是专门制作的,为了便
于携带是可以容易折叠的。借助于内隐记忆,H.M.很快学会了折叠拐杖,最
后,折叠的速度甚至超过了他的指导老师。如果问为什么需要使用拐杖,那他
就会动用他的外显记忆,但是,他因为之前的外科手术而无法使用外显记忆,
因此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Kosslyn,2003)外显记忆与内隐记忆的区别
是,人们可以有意识地想起所有信息;外显记忆的内容可以在提取后进入短期
记忆,并在那里进行处理:然后思考所提取的信息并加以利用,最后理解新的
学习内容。训练有素的秘书还能记住键盘上的字母顺序并流利地背诵出来吗?
要完成这个任务,她就必须动用外显记忆。
陈述性记忆。如果问一位秘书,键盘上从上往下第二排右数第三个是什么
字母,她就需要明显储存在陈述性记忆中的知识;这是实际的知识,是可以表
达和“阐释”的知识。陈述性记忆储存概念、定义、人名、日期和事实;这是
一种“知识,即”(我知道,埃菲尔铁塔是巴黎的一座著名建筑)。插图6.4表
明,塔尔文区分了语义记忆(储存一般知识的记忆)和情景记忆(经历记
忆)。如果问一个人,法国的首都是哪个城市,或《浮士德》的作者是谁,他
也许已经不记得自己何时何地知道这些答案的。一般知识的习得时间和地点都
消失了,只有关于这个世界的一般知识,比如,规则、概念和事实保存了下
来。
相反,情景记忆储存了人们亲身经历的、仍然还能记得的事情;人们还知
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我还记得18岁生日时的庆祝活动。”“我现
在还清楚地记得,我昨天的网球对手以他厉害的正手攻击给我制造的麻烦。”
“今天我还清楚记得,第一次坐飞机去西班牙时,在飞机起飞以前,一位友善
的空姐给了我彩笔和画本,我整个旅途中都在画画,而没有朝窗外看一眼。”
上述一个大学生对自己在两年前的九月的第三周的周一下午在
做什么这个问题所作的回答,就应归功于运转明显良好的情景记忆。
人们所说的自传记忆,是储存的所有生活经历;当一个人设计个人形象
时,就要动用这种记忆中的内容。(Fivush,2001)一个人如果没有这种自传
记忆,就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尽管语义记忆和情景记忆都属于陈述性记忆,但神经学的研究结果证明,
如果要完成这两种记忆形式的任务,就需要激活大脑的各个部位。
(Wiggs et al,1999)
程序性记忆。内隐记忆存储的知识内容是“记得的”,比如可以“改写”
为:“我知道怎样拉小提琴,怎样骑自行车或怎样使用电脑键盘。”塔尔文称
这种知识内容为程序性记忆,是运动过程的存储器。在这个存储器中还存储经
典条件反射(见第214页及以下几页)和操作性条件反射(见第231页及以下1
页)的学习结果(即习得的刺激—反应关系)。比如,程序性记忆能够使人在
看到某张照片时回想起因为与画面上表现的事件形成生条件反射而产生的感
情。(Tulving,1985)
记忆内容的组合。如果图书馆里的书籍随机摆放在书架上,那么读者为找
一本书就得花费相当大的精力,甚至很可能做无用功。馆藏书刊没有经过整理
和组合,图书馆的使用率就会极为低下。同样,如果长期记忆中的知识内容没
有经过整理,就不能被提取。但是,人的大脑是如何整理知识内容的呢?记忆
心理学家对这个问题已经研究了很长时间。在餐馆里,如果顾客很多,用餐量
很大,那么,有时就能发现,长期记忆也是按照一定规则整理知识内容的。对
一个无需作记录就可以记住二十种菜品的侍者的系统研究表明,这个人对全部
菜品按意义作了分类。如果妨碍他的这种整理能力,他就不能完整地记住这些
菜品。(Ericsson & Polson,1988)此外,还需要提到的是人人都非常熟悉
的体验,因为这种体验平均每周就会出现一次,年龄越大,出现的频率越高:
话在嘴边,就是说不出来。(Brown,1991)
话在嘴边现象。人们都有过这样的体验:某一个单词自己肯定知道,“就
在嘴边”,但就是想不起来,需要拼命去回想。罗杰尔·布朗和戴维·麦克尼尔深
入研究了这种体验,并获得了关于语义记忆的顺序的有益启示。
(Brown & McNeill,1966)年龄越大就越有这样的体验(Heine et al,
1999),会让人觉得非常沮丧;但这为记忆研究提供了极有教益的启示:储存
的记忆内容怎么会“丢失”,又怎么能重新提取。(Schwartz,2002)比
如,布朗和麦克尼尔问测试对象某种小船的名字,这种船在港口、在日本和中
国的河流上,靠摇动船尾的橹航行,多半也使用帆。两位研究人员还问:“船
员有时拿在手中,用来确定船的位置的仪器叫什么?”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一个在关键时刻想不起来的词,测试对象能用什么方
法来表示。通常情况下,他们能答出音节的数量和开头的字母。比如:他们努
力回忆“Sampan”(舢板,日本和中国的一种小船)时,能想起的名词有
“Siam”、“Sarong”或“Saipan”(臆造的),有人还想到
“Dschunke”(中国的一种帆船)、“Hausboot”(家用小船)或
“Barkasse”(大舢板)。测试对象寻找的“就在嘴边”的词,说出来却是错
误的,这些单词的共性,使布朗和麦克尼尔断定,长期记忆中的单词不仅是根
据声音特征(“Sampan”、“Saipan”和“Sarong”的发音很相似)存储的,
而且还依据视觉特征(“Sampan”、“Saipan”和“Sarong”的拼写很相
似),甚至根据意思(“Sampan”、“Siam”、“Sarong”和
“Dschunke”都是远东的物品;“Sampan”、“Dschunke”、
“Hausboot”和“Barkasse”都是船的名称)存储的。可见,在人的记忆中,
一个单词显然不像一本书在图书馆那样,放在某个位置,人们有时能说出一个
要找的词的很多特征,却说不出这个词,因为明显找不到其他重要的特征。因
此很多人也难以说出插图6.5所示的仪器是“六分仪”。
如果有一个单词“就在嘴边”,通常有助于发挥“自由联想”,即挖空心
思,回想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想起的尽可能多的单词。由于在长期记忆中存储的
具有共同特征的单词彼此是有联系的,所以迟早找到要找的单词,是非常可能
的。当时有些心理学家就认为,长期记忆具有组合,即整理自己的内容的功
能,因此有些记忆研究人员称之为网络,因为他们认为,记忆内容像一个彼此
交织在一起的网络。一种现在看来虽然已经陈旧,但依然值得一提的网络理论
试图解释,语言信息是如何按意思组合在一起的。
语义网络。亚里士多德早就提醒人们注意,单词之间是有联系的。如果请
一个人列举以字母A开头的单词或红色的物品,那么利用相似性的组合原则就可
以找到答案。因此,救火车和樱桃这两个单词之间就存在联系,因为二者都是
红色的。如果问人们,他们听到面包这个单词时,自动想到的另外一个词是什
么,很多人都会回答说是黄油。网络理论认为,长期记忆的顺序就仿佛是很多
单词交织在一起的网络。如插图6.6所示,这种理论称单词为节点。一个节点就
是一个单词——比如“街道”、“房屋”、“苹果”或“紫罗兰”——,它们
通过通道与其他节点相联系。
|


